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的许多学者开始以革命的国际主义和与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开展中国问题研究,并相继成立了—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1920年在圣被得堡和莫斯科分别建立了东方学院,同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建立了东方系,1921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了全苏东方学家学会,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了中国学研究所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发展,苏联出现了新一代的中国学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或是到中国进修学习,或是作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顾问和翻译参与了中国的革命。这一代学者以自己的亲生经历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们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分析,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著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苏关系也进入了“老大哥”与“小弟弟”的时代。在这种气候下,苏联中国学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许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中国研究进一步升温。为培养更多的人才,莫斯科东方学院、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均扩大招生,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一些高等院校也都增设了有关中国的课程,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研究机构和人才培训中心,促进了新时期苏联中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并使其研究逐步伸向社会科学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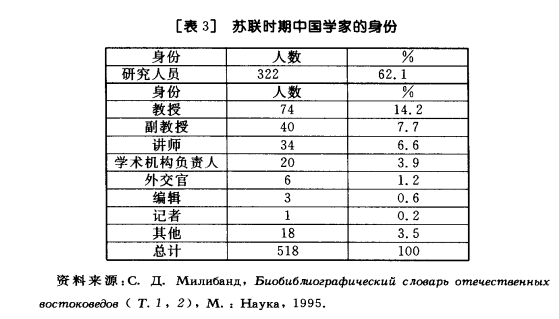
20世纪60—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发生变化,并很快影响到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许多高校停止了中国学专业的招生;由于在这个研究阶段,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破裂,苏联史学界根据苏共中央的旨意,加强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宏观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著,许多为通史著作,如远东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共党史概论》(1972)、《古今中国史》(197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概论》(1983)。有的著作有一定的学术性,而绝大部分为政治宣传品。
在80年代中期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前,由于中苏关系开始解冻,特别是在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苏联学者又恢复了同中国同行的直接联系,苏联史学界改变了反华立场和批判口气,重新谨慎地研究和报道有关中国社会和改革开放的信息,撰写一些介绍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如М·雅科夫列夫的《邓小平政治肖像》载《今日亚非》1989年第1期、Ю·М·加连诺维奇的《邓小平的个性、命运和政策》(1989)、В·Ф·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2册(1991)等。苏联学者改变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批判态度,不加评论地介绍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生平事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俄两国交往的密切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俄罗斯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机构、研究队伍以及研究领域和内容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机构方面的最大变化是出现了一批新的有关中国研究与汉语教学的机构和学术团体,一些原有的机构或团体扩大了规模,科研经费由国家拨款改为多渠道筹措。这些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系统之中。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学术机构出版了学术通报和学报,《远东问题》、《近现代史》、《亚非人民》等杂志经常披露中国的重要历史文献,正面宣传、介绍中国,研究中国经验。其成果如Л·П·杰留辛的《中国的改革与马克思主义》(《东方》杂志1992年第5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今日亚非》杂志1993年第10期)、《邓小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В·波尔加科夫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等。 |